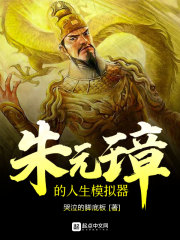补书网>大明:从边军开始覆明灭清 > 第267章 崇祯的天塌了(第5页)
第267章 崇祯的天塌了(第5页)
他痛心疾首地环视一周,将众人,尤其是那些激愤的言官和倒霉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尽收眼底。
“凤阳之祸,实乃本朝开国未有的奇耻大辱!”
“本阁身为首揆,未能洞察先机,亦有失察之责,自当向陛下请罪!”
温体仁先以退为进,姿态放得很低,但他随即话锋一转,又开始甩起了锅:
“但,祸根究竟何在?!”
“我认为,不在庙堂中枢,而在地方大员颟顸无能,玩忽职守!”
他猛地指向那份来自宿州的塘报,如同手握铁证:
“诸公明鉴!”
“流贼围城之前,凤阳巡抚杨一鹏和守陵太监杨泽在干什么?他俩可有积极布防?可有整饬军备?可有安抚民心?”
“没有!”
“反倒是每日醉生梦死,沉溺笙歌。”
“更有甚者,巡按御史吴振缨,面对百姓控诉太监杨泽的罪行时,他竟然闭门三日,拒不受理!”
“吴振缨坐视民怨沸腾,最终酿成守陵部队倒戈的大祸!”
“此三獠,实为中都陷落、皇陵被毁的首恶元凶!”
“至于兵部调度……”
温体仁的声音骤然变低,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张凤翼,
“张部堂或有疏漏,可究其根本,仍然是杨、吴几人在地方上未能恪尽职守,致使贼势坐大,终成燎原之势!”
“我中枢纵然有良策万千,但仍旧还需要地方官员尽力执行才是。”
温体仁一番话,看似条理清晰,逻辑严密。
但实则还是推诿之言,经过他一番忽悠,成功地把责任精准定位在了凤阳地方官员身上。
巧妙地撇清了内阁中枢,特别是他身为首辅的领导责任。
同时,也给了兵部尚书张凤翼一个台阶,尽力拉拢部堂大臣。
此话一出,不少官员,尤其是温体仁的门生故旧,立刻心领神会,纷纷附和:
“首辅明鉴!正是杨一鹏、杨泽、吴振缨之流误国!”
“地方糜烂至此,中枢纵有千策亦难实施!”
“当务之急,是严惩首恶,以儆效尤!”
可与此同时,也有不少看不惯问温体仁的御史言官站了出来,提出了反对意见:
“温首辅此言差矣!”
“杨一鹏、吴振缨之流罪该万死,不假;但中枢调度,庙堂决策,岂能置身事外?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