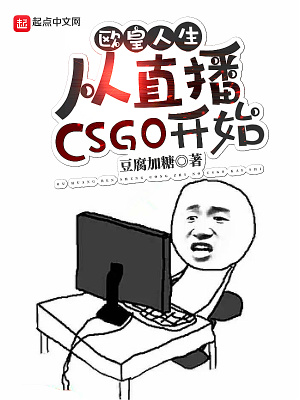补书网>秀才娶了兵 > 第156章(第2页)
第156章(第2页)
“我都听到了,我按你说的办,安心种地,护着一家老小平安。”
“那,那就好了……”
陈秉正将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,继续用湿布擦拭他的额头、脖颈、手臂。可是钱老板仰着的头颅已经失去了最后支撑的力气,重重地落回那堆稻草里。眼睛还圆睁着,望着头顶那片无尽的的黑暗。
一滴浑浊的泪,从他干瘪的眼角缓缓滑落,瞬间便不见了。
陈秉正慢慢放下了手中的那块湿布。他伸手将钱老板的眼睛合上,脱下自己的外袍,盖住钱老板的面容。
他敲一敲铁栏杆:“人已经没了。”
“多余弄这么一趟。”
狱卒嘟囔道,“我叫人来收。”
陈秉正站起身来,望着外面走廊里的一盏油灯,火苗突突上窜。走廊尽头,有个黑色的影子,立在原地,默然地看着被抬出去的尸首。
那是郑越。
等尸首在他视野中消失,他才缓缓说道:“请陈大人……陈秉正到议事厅问话。”
议事厅里点了两个炭盆,炭火正旺。郑越叫人解开他的手铐,关了大门,又指着凳子道:“快坐。”
陈秉正没了外袍,只觉得膝盖里麻痒得厉害,像是蚂蚁在乱爬,他不由自主地往炭盆边上凑,伸出手烤火。
郑越将身上的斗篷脱了,披在他身上:“将自己的衣裳给人做裝裹,你倒是好心胸。”
陈秉正将腿伸直了,微笑道:“你将衣裳给一个囚犯,也不遑多让。”
郑越叹了口气,也坐下了。两个人隔着火盆,只看见红色的炭从中间爆裂开来,噼啪作响。过了一阵,他才开口道:“姓钱的……死了一阵子了?”
“不到一个时辰。”
陈秉正淡淡地回答。
郑越眼中忽然闪过一丝莫名的恐惧,随即他抬起下巴,“这人是出了名的奸商,作恶多端,就该死。大牢里死个犯人,太寻常了。”
“是。”
“我交代牢头,给他弄口好点的棺材。好歹是济州人,算是乡亲。”
郑越闭上眼睛,“你还记得吗?当日钱家一跺脚,整个济州都得抖三抖。他说粮食涨价,一条街都得哭。”
“他也是肉体凡胎,有生老病死。”
“他落在大牢里,跟一条狗,一头猪也没什么分别。说打就打,说死也就死了。”
郑越搓一搓手,脸颊有点红,“还是科考当官好。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,果然属实。其实他这个人是真不聪明,当日只要他嘴上不那么硬,我或许还能放他一马……”
陈秉正心中一跳,只觉得他的话又多又密,全不是平日的做派,“郑兄,你怎么了?”
郑越咳了一声,“姓钱的死了,有些线索又从中断绝。万一巡抚他们要对你用刑,我便阻挡不住。案子拖得越久,只怕对你越不利。”
“钱老板生前……”
“什么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