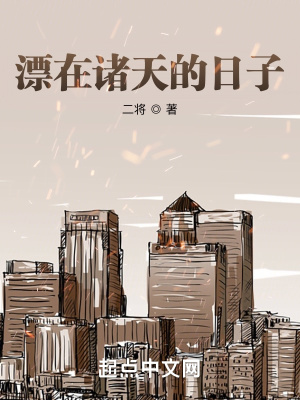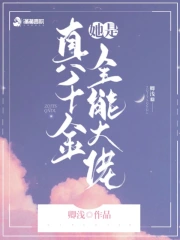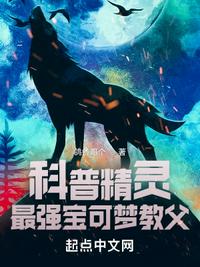补书网>三国:昭烈谋主,三兴炎汉 > 第392章 朝中的势力很顽固但可惜他们遇着了李相爷(第15页)
第392章 朝中的势力很顽固但可惜他们遇着了李相爷(第15页)
科举考试前三日,京城九门涌入考生及随行人员数以万计。
客栈早已客满,许多人家腾出空房租赁,价格翻了几番仍供不应求。
纸墨笔砚店铺前排起长龙,书坊里历年试题被抢购一空。
连代写家信的摊子都兼做起考前辅导的营生。
城南贡院外已搭起无数帐篷,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:
“状元糕诶,状元糕!”
“吃了必中状元哟!”
“文昌笔,文昌笔。”
“孔圣人开过光的!”
是夜,李翊微服巡访至贡院外。
见如此盛况,捋须微笑。
随从问道:“相爷因何发笑?”
李翊背着手,唇角笑意不减:
“我笑商贾机巧,借科举牟利。”
“然转念思之,若非陛下开科取士,洛阳安得如此繁荣?”
“强兵富民,本就是相辅相成啊。”
那随从见缝插针地说道:
“这些都是相爷您多年的功劳,若非您一时操持此事。”
“国家安能将科举推行下来。”
李翊笑着摇了摇头,笑意直达眼底。
“我不过是做了一点微末的小事,不求世人记住。”
“倘若侥幸,后人再提到老夫之时。”
“说李某确实为百姓做了一点实事,那老夫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大考之日,晨钟未响。
贡院外已是人山人海。
兵士持戟而立,维持秩序。
“诸生听令!按籍贯列队,查验身份后方可入场!”
礼官高声呼喊。
一名青衫少年排在天水郡的队伍中,前后多是年长之士。
有人见他年轻,笑问:
“小兄弟年几何?便来应试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