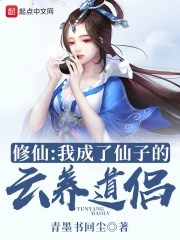补书网>天子宁有种 > 第一百八十一章 战局(第7页)
第一百八十一章 战局(第7页)
刘仁赡站在城楼上,观察着城下的景象。他捋着下巴的胡须,说道:“听说周军准备将正阳的浮桥移到下蔡?”
他心里猜测周军究竟在打什么主意。
难道周国朝廷认为淮河上游的诸城都没有攻陷,那地方地形太宽阔很容易受到唐军的攻击?
据下蔡方向回报,周国的几道浮桥,选的地方倒是有点讲究,在淮水一个急流的拐弯处,形成很大的曲度,下蔡就正好在水流放缓的缺口位置。
河面北边的地势平坦开阔,渡河之后可以很快的排列阵型,视野也很好,不至于有被偷袭埋伏的风险。
一个将领从石阶走上来,单膝跪倒禀报道:“禀节帅,兄弟们已在城南挖了地道,四面安上了瓦缸派人值守,若是敌军把地道挖进城内,动土就能听到动静。”
刘仁赡点点头,回顾众将道:“死守不是办法,咱们不能坐以待毙,如今朝廷大军各路来援,周军早已自顾不暇。而且周军久攻不下,人疲马乏。若能趁此机会打周军措手不及,得了一场大胜,周军的军心必定涣散。”
部将们忙以没有得到皇帝同意为由劝阻。因为大伙儿都不想出城去进攻……淮水那边远远看去还有成片的帐篷,看不清究竟还有多少人马。
双方兵力悬殊太大了,大伙儿觉得能守住城池已是十分不易。
此时一旁的刘彦贞突然开口道:“周军野战凶悍,我军唯有水战方能一拼,贸然出击风险太大。”
先前刘彦贞被任命为北面行营都部署,率大军支援被围困的寿州城,南唐主李璟对他寄予厚望。
可他却轻敌冒进,本想趁机偷袭回防的周军,谁知在正阳以东被李重进大败,仅带着数十名亲兵逃进了寿州城。
见识过周军战力的刘彦贞,此时让他再直面周军,确实有很大的心理阴影,更别说对方攻城的主将正是让他吃了大亏的李重进。
刘仁赡摇头道:“但凡守城,死守不是上策。这些天周军大量伐木,做了许多攻城器械,定是要准备猛攻寿州。坐以待毙不是守城之道。”
刘仁赡心里对刘彦贞有些鄙夷,明明当时自己派人劝阻过他。
可结果如何?把军队、粮草和战船,全都白送给了周军。他自己倒是厚着脸皮跑回来了。
刘仁赡觉得若是换作自己,早就当场拔剑自刎了,哪里还有脸苟活着?
但想是这么想,他却没表现出来,而是指向西北方的营地:“那边定是李重进亲率的侍卫司精兵,气势并非负责攻城的杂军丁壮可比。周军虽看似兵多,但精锐不足万人,且都远离城下营寨,攻城的这些人马不足为虑。”
刘彦贞闻言,张了张嘴却没再说什么,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没资格插手对方的安排。
有部将拜道:“今我等被困寿州,幸有节帅坐镇,天佑我等呐。”
另一人附和道:“官家是不会坐视寿州被围的。何况节帅在此,官家就是愿意丢了寿州,也不愿意丢掉节帅。”
众将虽然依旧心里有些没底,但大伙儿都很相信威望极高的刘仁赡。他的威信都是凭着待将士如亲人、领兵打仗无数次积累起来。
刘仁赡立于城楼之上,又观察了一会儿,心中渐渐有数,他淡定吩咐道:“到时我军步骑从定湖门出城,得手之后先焚毁淝水河边的器械,接着调头向南进击,再烧毁正面的攻城器械,然后从通淝门入城。”
身旁的偏将正要领命,又听他补充道:“骑兵须如疾风掠野,一击即走。出城之后不要恋战,骑兵先打他个措手不及,冲散其营,别让他们集结成阵,步军随骑兵掩杀。”
刘仁赡下定了决心出战,遂从军中挑选了精锐步骑,开始悄然准备。同时任命自己的长子刘崇讃为前锋指挥使,让其率精兵随时出击。
不过关于何时开城出击,刘仁赡也要谨慎思量,需要捕捉他认为有利的时机。